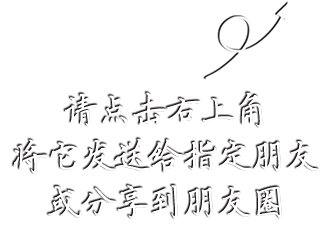□ 王苏恩
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傻瓜式”的经典人物形象,如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中的傻瓜班杰明,或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傻瓜威尔逊。被各种社会权力范式指向下集合而成的“傻瓜”角色,默默承受着愚弄与嘲讽的命运之轮,也始终秉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淳朴与怜悯。《傻瓜吉姆佩尔》作为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主人公也是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傻瓜形象。正如余华评价这部小说般,“吉姆佩尔的一生在寥寥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
吉姆佩尔是小镇上的一名孤儿,从小就被镇上的人们视为傻瓜,每个人都要愚弄他一番,“吉姆佩尔,天堂里有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生了头小牛;吉姆佩尔,有头母牛飞过屋顶,下了好些铜蛋。”备受嘲弄的吉姆佩尔选择了隐忍与相信,“书上说,最好一辈子当傻瓜,也不要一时作恶。”为了那个从未抵达的灵魂属地,他甚至面对妻子埃尔卡明目张胆的不忠都选择了缄默,吉姆佩尔深知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一切的挣扎都将沦为善意的徒劳。在镇上所有人的眼中,吉姆佩尔的存在像一个无生命的假人般苦寂萧疏,他的愚笨成为其存在于世的唯一意义。
百般愚弄的处境之下,当邪恶之灵怂恿吉姆佩尔在面团中撒尿,有过一瞬报复之意的吉姆佩尔还是选择把尿液面包从炉膛里取出,转身离开,四处流浪。吉姆佩尔完全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善的,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至善”的存在,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愚笨”来应对世界的愚昧与茫然。正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信仰与真实间的裂痕”般,吉姆佩尔并非像村里的人一样陷入信仰身份的虚空,而是自始至终恪守住信仰的“本真性”,用一派坚守人间的欢喜之态,来抵御现代社会下所迷恋的自由与伪善。
辛格赋予了短篇小说一种独特的风格——故事文本背后人类精神世界的良善希冀,用朴实无华的故事本身,来呈现一种永不过时的文学力量。在辛格的回忆录中,他提到,“我还是与一切保持距离。我已向忧郁投降,成为它的囚犯……我梦想着一种人道主义,一种伦理,其根基乃是拒绝为邪恶——那上帝带给我们的,且准备将来继续带给我们的邪恶——辩护。”诚然,辛格深知骄傲的弊端与形式的诡辩,他将写作视为一种“暂忘人类灾难的手段”,如同看似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美德与善的吉姆佩尔,实则却是他对于人类生命姿态的理性凝视,一切的至暗与至善都将注入历史的地平线中,为之留存的是那些小人物背后最为纯粹且炽热的灵魂。
在歌德的“上帝神秘的作坊”里,人类妄想通过种种荒谬来探寻生命的存在之根。而辛格则始终反对这种“实验性文学”的象征性追溯,“文学当然可以描述荒诞,但文学本身绝不能成为荒诞。”辛格的第一叙事视角,是在用一种最为朴实的手段还原吉姆佩尔看似荒诞且无意义的一生背后所折射的理性光辉,傻瓜吉姆佩尔的处境既是一部关于弱者的信史,更如利剑般指向镇上的所有“施暴者”。
“这个世界全然虚幻,但与真实世界也只是隔了一层。”四处流浪后回到弗兰姆普尔的吉姆佩尔,依然和孩子们分享着关于“魔鬼、魔术师、风车”的猎奇故事。小说结尾的一段话引人深思:“大限来临时,我会高高兴兴地走。不论那里有什么,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算计、没有嘲弄、没有欺骗……在那里,即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被骗。”